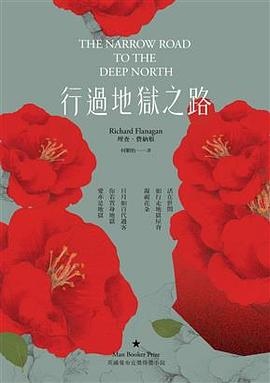
行過地獄之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Richard Flanagan)
"行過地獄之路"是澳洲作家Flanagan的作品,從英文書名"通往北方的窄路"是看不到地獄的意思.但看完之後,覺得這樣翻也挺好的,甚至覺得書的禎裝也對了.是因為個人以為這小說是本建立在反諷,對立暗喻的故事.用表面的美麗燦爛光明鮮豔來呈現兇殘噁心殘忍荒唐的真實世界,並對這種呈現法語意念表現出的假意世界提出一種隱性唾棄,所以表面上故事人物用了大量的西方詩歌日本緋句來呈現個人的心情與意圖,但實際上深究這些詩歌的意境與這本小說人物呈現的處境根本完全不同,甚至相悖.而我以為這是故意的,就是要用這種反面假掰的手法來諷刺假掰的世界.這種呈現法就像現在年輕人開玩笑的網路用語:"通往北方的窄路(讀作行過地獄之路)",所以才說翻成這書名也能接受.
說用了大量的詩歌與緋句,其實主要是四個人.一個是寫出"通往北方小徑"的松尾芭蕉,一位是小林一茶,這兩位緋句的作家,前者作品主要是寫出他旅途中對於大自然所感受的身心反應,而小林一茶的作品則主要唱應人道精神:在於對抗強勢扶助弱勢.另外兩個作品都是書中主角人物杜里戈醫生常用的話語來源,一個是書中幾處都能見到的"向風車進攻",這很清楚說的是西班牙作家賽萬提斯的唐吉軻德,另一位則是英國詩人丁尼生寫的"尤利西斯",主角死前再度引用的便是尤利西斯的部分.唐吉軻德的意喻挺清楚明白的,一種傻意的理想追逐者,而尤利西斯這詩則是意喻即便生活困苦也要積極生活的意思.明白了這些作家作品的意思,再讀回小說內容,才能發現這裡面意義對比的意趣,當然可能並無別人這樣看,不過接著看內文大概,便能知曉它的創破性,其實從簡單的結局思維便能猜想,小說裡犯下戰爭罪的日本戰犯不但個個壽終正寢,有人活到105歲,甚至安享自得的逝於榻上,身邊安放讓身心安樂的緋句作品,而反觀戰俘們返家後卻逐一遭遇不幸,妻離子棄,主角更是在山火中車禍喪命,難道這樣會是一本符合普世價值的戰爭小說該有的結果?這不讓不讓人進一步的深思這樣佈排的可能!?.
杜里戈是一個澳洲的外科醫生,年輕時是位上校軍醫官,二戰時隨軍被派往馬來西亞,後被日軍俘虜,在戰俘營中,他是官階最高的人.而他所處的戰俘營有一個特別任務,就是被強迫要在泰國往北修築一條通往緬甸的鐵路,杜里戈是指派澳洲戰俘到工地工作的指揮官,但本身不用下地工作,因此他有許多時間來思考與發呆,因此被迫不斷的回想到過往的日子,唯一任他牽掛的是他在阿德雷德偷情的對象,他叔叔的老婆艾咪.又因為它是外科醫生,必須隨時醫治身體受創的同袍,在這個赤道雨林遭日軍長時間強迫工作的澳洲戰俘,面對伙食不佳,隨時要瘧疾登革熱霍亂痢疾的威脅,經常餓病交加,加上日軍動輒體罰,1000多人的戰俘營轉眼間只剩下幾百人能勉強工作而強迫它們工作的戰俘營真正指揮官有兩人,發號施令的古田大佐,與實際執行任務中村少佐.為了達成天皇下達的命令完成鐵路,兩位日軍軍官展現出了各種可能的嚴酷指令與手段,加上缺糧缺藥品,許多戰俘都染上疫病不曾得治,因為根本沒有藥物,那霍亂痢疾瘧疾該有的患者樣貌,與身體的結果都透過小說文字真實的呈現,至於毒打體罰由底小黑賈狄納因為他人的怠工而被誤認是不工作遭到軍曹活活得給打死最為令人驚心.而不論杜里戈如何求情,或是擺出不合作的態度,都無法動搖這兩位軍官的意志,本來杜里戈還能保持一點正面的心態,但在小黑死後,他後悔沒有早一步提醒中村小黑早就被疫病迫害到神智不清應該停工可能是造成小黑死亡的間接因素而感到沮喪,又接獲新命令要選出100位戰俘出發到100公里外的地點從事構工,但其實已經沒有健康的戰俘,被選上的人幾乎可能就是有去無回而感到頭痛時,收獲家書,得知艾咪可能已經喪命於火災,此時的他可以說已經完全崩潰.已經完全喪失希望的他,自此開始過著一種奇異的生活,因此戰爭結束後,他也沒有立即返鄉,而是在其他地區繼續為戰爭後續的處置.會到家鄉後,他表面與未婚妻愛拉結婚,過著外人看好的婚姻生活,又因為專業上得到發展成位眾人尊敬的人物,但實際上他的家庭生活名存實亡,夫妻生活是假面,他本人經常與不同的女人偷情.而古田與中村戰後回到日本,古田逃過戰犯的指控,還因為曾經在中國東北參與活體取器官的實驗,被拔擢為"日本血庫"的高幹,而中村先是隱姓埋名躲過追捕找了份正常工作謀生娶妻生子,等追緝時間一過才以本名出現,後又到了日本血庫任職再次做了古田的部下,但兩人生活愜意自在,戰爭在它們身上其實根本不留存甚麼記憶,如果有那也自我解釋為遵從天皇的旨意,甚至中村自認是受害者,他們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在戰爭期間曾經做過甚麼,宛如完全正常的家庭生活.古田死後旁邊擺著松本芭蕉的奧之細道用枯葉夾著一頁""日月乃百代過客 年亦旅人耳",中村死後劉下的絕命詩"冬冰 化為清水 我心分明",反而那位必須聽命兩人負責打戰俘的韓籍軍曹崔相敏被列為戰犯,被執行了吊刑,而後杜里戈在雪梨的路上與艾咪擦肩而過,兩人都認出對方卻沒有相認,因為沒有必要,過去的時間與日子早已回不來了,艾咪當時以身染癌症,一年多後病亡,而杜里戈則在參加一次家聚時在山區面臨突發山林大火,為了拯救妻兒,他開車衝撞下得以獲救,這讓他感到家庭的存在,但是不久的某一天,杜里戈半夜開車不明原因出了車禍,他終於結束了一生,也結束了他自入戰俘營以後就只剩下軀殼的生命.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充滿各色詩句與意境架構的時空,但實際上它想要呈現的就是戰爭在實際戰傷者或戰俘身上所留下的疤痕與記憶的頑固性.作者試圖表達這些傷痕,記憶與我們這些後代所受獲經歷的大不相同,那些冷冰冰的文字或是事無關己的記述是不可能觸碰到戰爭殘忍的核心.甚至於古田,中村所留下的緋句,絕命詩,有哪一點不表現出純潔光明自認無塊天地之愾!?相對的,那位經常講出"向風車進攻"的杜里戈在戰後的二十多年裡又哪裡還存有一點這樣的理想心態,因為他對理想的希望與執念,在那天收到了艾咪死訊與必須與100位同袍話別時,就已經畫下了句點.而作者在這裡安排了他家庭遭遇山火的蒙難,多少也表示了他捨掉了唐吉軻德的念想,而成了回歸現實的桑丘,意味著這場戰爭的蒙難,要直到此刻才有一個短暫的了結.而這之前他的生活正如地獄,不只戰爭時處在地獄,對於戰俘來說這樣的地獄折磨記憶或伴隨著他們直到真實肉體死亡前甚至不能消滅.所以我會以為作者正是借用了這些假掰的詩詞來呈現現實世界裡對於戰爭的虛偽看法,以為它結束了它就對人的影響消失了,彷彿我只要把它當成是歷史書籍紀錄的文字就能毫無罣礙的接受它,或無關緊要,或事不關己,一如古田中村,也如小說故意呈現出日本優美緋句文字,不論是從自然旅遊來的體悟或是宣揚人道精神,其實是暗含玄機的諷刺戰爭的殘酷被這種假面文藝給掩蓋了,而作者就是要拿戰俘所受的地獄之行,來對比通往北方的窄路,也許某些人早就忘記了自己曾經發動過戰爭,忘卻讓他人受盡痛苦的地獄折磨,但是那些有過相同經歷的人不會忘記,他們的後人也不會忘記,因為作者Flanagan本身就是戰俘的後人,所以,這小說這樣特別的方式,絕對不適偶然搭建的,作者聰明的以優美的罵人方式,說出了他要說的故事.
單就戰俘營的故事,與那些折磨人身的過程就值得人們來看一回這本小說.至於其他衍生的看法純屬我個人猜想,也許並不具備太過重大意義,參考即可.對那些緋句或詩句沒有感覺的人,不妨就將它當成假掰裝飾的部分也無不可.以上.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