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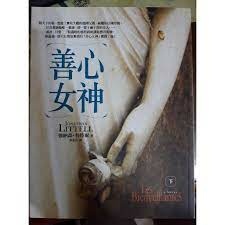
善心女神(Les Bienveillantes,Jonathan Littel)
" 人會死,希臘人是人,所以希臘人會死.人會死,草會死,所以人是草".這種怪異的邏輯稱為三段論證法,此意的法文則是sullogisme,希臘文稱為sullogismos,意思是"廢話".這類邏輯悖論並不陌生,每天的政論節目內容基本上都這樣論證的循環.不過sullogismos除了做無意義的吵架外,也可做為是某些犯下滔天罪行者自我辯解的一種言行方式.
這次連四部的小說裡,"善心女神"份量最重,近100萬字,是其中唯一的法文小說,所以放到最後看.這部不論份量,文字看似都與類型文學接近,這樣看是部面對讀者較友善的作品,但實際上並不如此,長篇累牘且意識串流增加了閱讀的疲倦感,從題材來說,這部就更不友善了,題材的原因讓它也能讓它被視為一種類型小說,只不過這樣的類型是特殊的."善心女神"是一部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類型小說",畢竟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書籍,電影,影視作品太多了,已經足以歸類成一種類型吧.它的不友善,除了事涉猶太人被滅絕,外加亂倫,弒母疑雲,都不會是常態閱讀者習慣的內容.因主角人設是個納粹國家安全局黨衛隊軍官,小說以他第一人稱視角來寫東線戰區蘇聯境內烏克蘭,高加索,在德國境內,在波蘭境內的集中營,滅絕營,奉令殺光滅絕佔領區內所有猶太人的德軍上下的各種作為,因此整本小說所顯現的血腥,暴力,殘忍等無法盡數的殘酷場景情境是一個接著一個,這對閱讀者來說絕對不是友善的故事.若說它與其他猶太人遭屠殺作品不同的是,這是一本黨衛軍軍官第一人稱角度的作品,跳脫了受害者的苦難或是黑色幽默的諧趣的慣見的作品角度,它是以"加害者"的身分來寫種族絕這樣的故事,且潛藏另一種罪咎觀點.
以納粹黨衛軍的視角來描繪猶太大屠殺事件不但觀察角度有異,甚至這樣的長篇累牘也出現了令人意外的觀點.就在我們以為這又是本加重控訴納粹滅絕手段的作品時,它的文本卻出現了許多屬於黨衛軍軍官的自我安慰與刻板認知的橋段,這些橋段與作為是主角人物麥克斯米連的人生遭遇是相關的.小說主角原本是一個法律學博士,對希特勒雖有景仰,對納粹推動的國族主義有強烈認同,但他自身並不仇恨猶太人,也沒有歧視其他民族的心理與知識條件.麥克斯米連加入希特勒國家社會黨的主要原因是想擺脫母親與繼父的管束,也為了追尋對生父的過往記憶與現實的求職需求而由法國回到德國.就他個人說,他在蘇聯,烏克蘭東歐境內奉命執行的滅絕任務,不過是基於對祖國的信仰,與認同.參與滅絕行動並不是他一開始就計劃好的,更非人生的必要追求,而是被整體大環境推動往前,一步一步地被推向眾人唯一或者是他們以為的最佳選擇.這小說除了加害者的視角外,自然也提出了加害者合理自己行為的說詞與理由,但這裡的言行合理化除了是居於黨衛隊軍官角色的必然推理外,多少也反映了作者自身想表達的觀點,作者其實未必同情或曾經試圖幫加害者開脫,但讀者讀完可能會有這樣感受.我以為他嘗試提出了一個疑問,就是人們是否能抵擋在大環境壓力下的不可能.這種不可能對於個體來說是無法逃脫的同儕集體壓力,是集體意志壓迫下所形成的一種自我保護不得不為而被迫參與惡行,那麼對於這樣的人究竟該如何看待呢?我以為作者並不在試圖幫德國曾經的罪行找開脫的理由,而是透過主角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巨細靡遺地將主角在二戰期間的生命歷程展現出來,讓讀者通過主角的個體故事,看到德國納粹的集體行為,並據此形成另一種觀點的疑問與判斷.誰都不會否認納粹犯下的罪行,但是,小說或者希望當有機會角色互換時,換做自己是身處其中的德國軍官與人民時,你是否也會做出同樣的行為?!,而你是否就因為沒有這樣的機會成為當時環境下的人而就擁有無限高度的道德高位,能因此輕鬆批判與究責當時的一般德國人或者是像麥克斯米連這樣的黨衛軍中高階居官,而這樣的重點就不在誰該罪咎,而在異位而處的思維態度.
從以上的角度切入,首先邁入眼簾就是主角麥克斯米連.表面上看,他是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法律專才,學識充沛,黨衛軍的二級突擊中隊長(少校),過往師從的老師或友人都在政府或軍方任要職,從職涯上看是一顆上升的星星,受到各方人士的尊重.但實際上不同於職涯表面藏在陰暗中的他,一位男同性戀,不見容於納粹的法律,只能在陰暗的廁所,夜晚的公園內與不知名的小男孩或是酒客進行超乎法律的行為,他還是一個與孿生姐姐發生亂倫關係,疑似生下雙胞胎的心理變異弟弟,他還是一位因為父親的不告而別長期怨恨並遠離母親與繼父的兒子,最終並可能殺了他們兩人.因為他還是一位欽慕家庭生活卻無法建立任何異性關係的男人.這幾種陰暗隱藏在有正常社交生活,官運與戰場運氣無往的不利的麥克斯米連二級突擊中隊長身上,正好呼應了主題"善心女神",一種雙面且複雜的代表意義,說是善心女神,其實不折不扣的復仇女神,且隱含這種復仇不達目的絕不終止,但終止目的在哪裡?可以說是根本沒有盡頭,即使被復仇者已經墮入地獄遭到各種折磨,復仇者依然不放手之意.
書名的"善心女神"源自希臘神話故事,復仇三女神,Alecto(阿勒克),Megaera(美嘉拉),Tsiphone(提斯豐),分別代表不安女神,忌恨女時,報施女神.她們在大地上追逐殺人凶手,特別是弒血親者,使他的良心受煎熬,發瘋發狂,在地獄裡,她們也負責對罪孽的亡靈執行懲罰,她們是希臘人最懼怕的神祇.但是明明是復仇三女神,卻又為什麼變成了"善心女神"呢?這其中有另外的神話故事.邁錫尼的阿伽門農進軍特洛伊,為平息海神的風浪,將女兒獻祭了.十年後,他毀滅特洛伊後凱旋而歸,但阿伽門農的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為了替女兒復仇,聯合自己私通的情人埃癸斯托斯刺殺了阿伽門農,奪取了政權.阿伽門農的兒子奧瑞斯提亞當時才十二歲,由姊姊厄勒克特拉托付給一位僕人後奔赴法諾忒的國王也是阿伽門農的妹夫斯特洛菲俄斯.奧瑞斯提亞曾揚言定要為父報仇.長大後,他按照阿波羅的神諭殺死了自己的母親,以及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殺人復仇固然對他而言天經地義,但按照希臘的法律,奧瑞斯提亞必須向"殺害他母親的人"即"自己"復仇.在此"復仇"的概念成了了無法調和的自相矛盾,於是復仇三女神糾纏著他,追到他到處流浪後發瘋.此時阿波羅指引他到雅典,阿波羅宣稱將在那裏給奧瑞斯提亞一個公正的法庭.經歷千辛萬苦,奧瑞斯提亞到了雅典,他伏在神像前請求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裁判,復仇女神也表示同意.雅典娜表示"這件案子奇特複雜,是人間的法庭幾乎無法判決的".'如果法官們難以判決,就由我主持審判.但雙方都得尋找證據和證人".奧瑞斯提亞為自己辯護,他表示殺死克呂泰涅斯特拉時並不把她看作自己的母親,而是把她看作殺害父親的凶手.阿波羅充當證人並極力為被告辯護,發揮了辯護的作用.他描述了阿伽門農被謀殺的慘景,認為這是滔天罪行.他聲稱,父親是真正的播種者,一個人可以隻有父親沒有母親,正如雅典娜是從宙斯的頭中生出來的.復仇女神加以反駁,指出弒母是十惡不赦的犯罪,殺死血親比殺死姻親的罪行更嚴重.辯論完畢,法官們進行投票,結果雙方票數相等,而雅典娜投出決定性的一票.奧瑞斯提亞被判無罪,獲得了自由.復仇女神不敢冒犯被宣判無罪的人,但仍表示對判決不服,並遷怒詛咒法官.阿波羅和雅典娜設法勸阻她們,說雅典人將把她們作為公正的無情的復仇女神來敬奉,復仇三女神因此也被被融入雅典,她們也最終放棄了復仇的權力,轉而成為繁榮的保護者,所以人們也開始稱她們為"善心女神".
對於麥克斯米連來說,他就是本書裡的奧瑞斯提亞,當然這種悲劇性的角色多少源於麥克斯米連自我的想像,他將父親的不告而別拋家棄子從此失蹤視為是母親謀殺了父親.於是就有了一連串的不見容於當時社會價值觀的行為.比如,因為認定了母親的這種弒夫的作用,他自幼即想辦法脫離母親與繼父建立的家庭,剛好藉由與孿生姊姊亂倫事件能夠離開,卻也因此自寄宿學校遭到其他男學生的性侵,所以他究竟是天生的同志,還是被導引的同志並不清楚,連他自己也迷茫,因為他的同志行為在他的夢裡與想像意識中其實常常與糞便,噁心嘔吐物相伴而生,但他卻又樂此不疲,特別是他在史達林格勒腦部中槍後,這種胡亂想像的意識與混亂一直盤踞著他的主要想像思維裡.而他唯一認定的愛與孿生姊姊烏瑪的愛,其實那只有身體的性愛,且只在幼時,種種的混亂不堪,與他表面的風光是完全大異其趣的,現實裡他是原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完全依舊自己的理性智慧行事,但這樣卻常遭他的唯一好友湯瑪斯嘲笑,湯瑪斯與他不同,相當懂得審時度勢,所以官位升得比他快,且常常料中麥克斯米連錯誤的選擇.這些情況一直要到他在東戰場吃足了苦頭,被同袍與上司合謀陷害遠調圍城史達林格勒,嘗盡了苦果,把無情冷血麻木訓練成自己的標誌,從原本想到屠戮戶面就覺噁心想吐,到後來殺起人來決絕毫不遲疑,甚至殺人已經成了夢裡或是無意識下的能夠反映的一種自我保護行為,在後半部的文本中,他幾乎是已經毫不遲疑的能夠舉槍殺人,甚至最後連湯瑪斯都被他打死了,且拿走他事前準備好的假的身分證明,逃出柏林,逃出德國,逃出戰後的戰犯審判.法律拿他沒有辦法,但那又如何呢?他早已經被復仇女神,善心女神的追緝給逼瘋了,而這裡的暗喻是,即使麥克斯米連曾經殺過一些人,絕大多數都不是他有主觀"殺"的意願,他都是被迫的,有所謂理由的,但殺人就是殺人,該給予審判,懲罰,罪咎.問題是誰來判決,誰來執行,又該給予何種判決,罪咎多久?.
同樣的概念,由麥克斯米連擴張成德國人,整個納粹德國.猶太人在整本小說裡成了沒有臉孔,名字,只是一個該被屠戮對象的代名詞.我們看到各色的納粹軍人,高官的言論,聽了各種說法,理論的,意志的,歷史的,政治的,甚至是宗教信仰的,皆曰猶太人該被滅絕,滅絕是為了德意志民族,為了德國發展,為了世界人類.從這些個體到集體的論點來看.難道這些人在殺人滅絕時是"主觀"的嗎?主動的嗎?他執行命令,聽從輿論,書籍,指引也是主觀的,經過思考的?還是一如書中所講的艾克曼(其實他就是平凡裡的邪惡的艾希曼)那樣沒有思考,沒有情感,他只是執行命令?對我來說,這個答案越來越難判斷,以前或許還會質疑人怎會沒有思考,獨立判斷,單純的集體意志的命令當作聖旨般執行,但現在越來越不確定,可能真的有不少這樣的人,即使今日依然大批的存在,但若真是如此,我們就該放他一馬?不該咎責嗎?因為酖春宣告無辜只是當時從眾也不能不該做為推卸罪行的藉口,而小說有意無意的暗示從奧瑞斯提亞的復仇矛盾循環,就是向殺人者復仇的行為本身也該受到罪咎則是有意無意帶出這樣的暗示,世人對於納粹,對於德國,對於德國人那段屠殺歷史的追究,特別是猶太人對於他們的追究是否已經過頭了,甚至這種罪咎可能已經形成這種復仇的矛盾無限迴路,也就是有必要像復仇女神的這樣一直追究下去嗎?.
敢於提出這樣的疑問,那是因為作者本身就是猶太人,其他人可能未必能或敢於寫這樣異端的題材.想藉由此探索將復仇女神轉變為善心女神的可能.所以從書寫的角度,作者大膽的使用了"加害者"第一人稱的視角,卻也隱藏著"奧瑞斯提亞"們另一種第一人稱思考的可能.這其實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小說,特別是若沒有點破這希臘神話引用的意思,可能讀者就是單純看了一本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故事兼德軍在東戰場的作戰史,然後加上各色納粹軍官對於屠殺滅絕行為的各種解釋方式與應對,也就是sullogisme的小說,但其實並不只有如此,這是值得去留心的地方.文本過長與大量的民族誌,語言史,民族遷徙與融合歷史加了它的枯燥度,當然一個人的悲劇與一個民族國家的悲劇來類比可能還是有若干不對等之處,但基本上我認為作者提出了相當值得思考的東西.以上.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