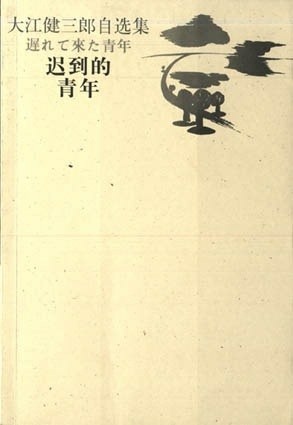
遲到的青年(遅れてきた青年, 大江健三郎)
"遲到的青年"意義上是大江健三郎的首部長篇,雖然是大江早期作品技巧未必成熟,但個人以為題材與穿透性算是尖銳有力,所以列在第三本閱讀,.這裡的"遲到"可以理解為"參戰"的遲到.也能衍生為人生道路上許多事情不及參與的遲到,而造成這樣的現象的原因主要便是前面所提參戰的遲到.事實上,這小說寫的是特殊的一群人,他們與作者相同,大約都在1930年代出生,在戰爭中度過童年,進入少年,青少年,然後突然有一天宣告終戰,且日本戰敗了
說是特殊的一群人在於在這段期間成長的人深受軍國主義思想教育洗禮,他們的全身心上下一體都是為了做參戰準備被打造的,而更遲到194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對世界懵懂未知時便進入了戰後,自然不像這批前輩必須與灌輸於身上僵固思想,相處,融合,對抗,戰鬥,"遲到的青年"中第一人稱的"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文本依據"我"的成長分成兩部,第一部的時間設定在1945年,當時的"我"尚是小學生,居然要面對戰敗的新時空,第二部時間則跳到1956年,"我"已經成為東京大學的大學生,是個被認為有前途的菁英分子,在高速發展的現代文明中,找尋著自己的道路.
"我"居住於四國的鄉野山村"山腳",童年時期的“我”跟其他人一樣,在軍國主義的教育與思想環境成長,耳濡目染下自然有著各種推動軍國主義思想教育者想創造的行為特徵,"我"很希望為大日本帝國犧牲,時常抱著快快長大能加入戰鬥讓帝國榮光的遐想,但是還沒有等到他長大,戰爭卻突然結束了,即將接受美軍監管的恐懼心理席捲了所有的人: “美國人會強姦婦女,屠殺男人和孩子,”,類似這樣的恐怖意象在多數村民的心理縈繞.而在混亂和恐慌中,進入"山腳"當地的美國大兵突然被村民打傷了,美軍要求交出兇手,但山腳村民卻利用這個機會陷害了當地的原住民"高所人",說是高所人打傷美軍,於是高所村民慘遭屠戮被滅村..同時原先在戰時被日本人欺負的朝鮮村落居民也趁機劫掠了山腳村民:"把日本帝國主義從朝鮮人民那裡搶奪的東西還回來!日本人都是小偷!",雙方關係變得緊張.而“我”並不甘心日本就此戰敗,他也不同於村民,在高所被滅村的事情上,他甚至出面去尋找兩個被通緝的高所人,想要救援他們,但可惜找到他們時,兩人已上吊,他還與朝鮮村落的小孩相處友善,後來他和朝鮮村中的朋友"阿康"約定好逃出山腳,加入"杉丘市"反美軍的戰鬥,但是他倆在抵達目的地的火車站時卻被警察逮捕了,並且搜出來有武器,又因為"我"所交代的朝鮮人和高所村事實沒有得到村民及家人的承認,"我"被投入了少年教養院,在教養院裡,朝鮮朋友阿康則趁機逃走了,在少管所的"我"一直寫信給媒體,揭露高所人被害的事蹟,但是卻被所長發現並狠狠揍了一頓,從此變得很沉默,他在教養院一共待了三年,
時間來到了1956年按照社會設定的成功標準,"我"考上東大政治系,試圖拋開過去成為一個受人注目的人,為此他加入了學生組織"戰鬥日本會",希望能在左翼團體運動中有所發展,他結識了保守派政治家澤田豐比谷的女兒澤田育子,並且因此搭上了澤田豐比谷,表面上看來"我"已進入人生順利的行列,但因為要幫澤田育子墮胎,收了一張開自澤田豐比谷20萬元的支票被他所加入的左翼學生組織發現,懷疑"我"是保守派派來刺探的間諜,收錢位保守派打探消息,因此被嚴酷的拷打,甚至被流浪漢強姦,為了報復,也為了自己的前途,他順著澤田豐比谷的思路加入到他的陣營,徹底整垮了左翼學生組織,並且得到了政治家的賞識和幫助,當未來看起來步入了他期待的軌道時,他又遇到了兒時的朝鮮朋友"阿康",由此想起了兩人最初的夢想,阿康想回北韓去協助金日成戰鬥,他則是想為日本帝國戰鬥,但兩人當錢都沒有依照當初的夢想,陷入了各自的困境,"我"因此為自己的作為而羞愧,為此,他違抗了澤田豐比谷用電視節目想揭發對手醜聞的手段,因此兩人反目,他被澤田豐比谷放逐,"我"自以為從此解脫了,能夠做真正的自己,但是他並不快樂,藉助毒品和荒唐的生活來自我放逐,甚至還在恍惚間殺了性虐殺了流浪漢,但此時澤田育子又懷孕了,她試圖和小情人撞車殉情,最後沒有成功,小情人身亡,她則成為一個毀容的人,這時已宣布要參加東京都知事選舉的澤田豐比谷需要一個男人來當孩子的父親,掩蓋澤田育子的醜聞,於是他又找上了"我","我"又變成了政治家的操縱的工具,他將娶澤田育子並赴巴黎定居一段時間,等待選舉結束,作為交換,他可得到夢寐以求的榮華富貴與前途,但是也必然陷入痛苦的深淵,幾經考慮,最終,"我"還是走向了自己曾期待又深深厭惡的道路.
做為玉碎思想調教出來的一代,在戰敗之後,思想的柱石與希望完全倒塌後,所有的人都陷在了虛無的時空裡.他們本來就沒有被教育要有"我",所以"我"這個概念在大江的小說裡其實非常的重要>從第一本開始到這第三本,長篇也好短篇也罷,大江作品裡的主角都是沒有名字的"我".一方面是集體主義思想中,所有的"我"與他,她是沒有分別的,是集體主義,軍國主義中所欠缺或割掉的要素,因此作品裡的"我"都有隱藏著要從集體中找回"我"的意義,與"我"的主旨,另一方面"我"究竟是甚麼樣子,該如何能找到,是在脫離集體後先呈現出單獨個體的"我",然猴才能在物質"我"的基礎上找到數於身心靈想情感特別或與他人不同意義的"我",很不幸的,在虛無主義瀰漫的社會裡,要先找到我,突然發現這個"我"是沒有意義,沒有目標,沒有思想,沒有追尋,因為一切的意義,目標,思想,追尋,都是別人教育的,都是別的人,與"我"無關.既然玉碎不在了,那頂替上來的是甚麼,"我"就會去蓋像追逐那個,於是戰後以金錢物質發展為先導的高速經濟追求成了"我"的主要追尋.
"遲到的青年"中的"我"則認為自己的精神喪失於1945年夏天的"遲到",“我”不及參戰,日本便戰敗了."我"感到自己的遲到是決定性的,無可挽回的,並造成了自由意志的缺失的陰影,認為自己無力改變.因此延續著此觀點對戰後青年一代來說,世上重要的事彷彿都是外力決定的,個人無法改變,這使得他們只能成為"性的人",沉湎於感官享樂,而無法變成“政治的人”,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改變明天.所以我們從閱讀大江的作品開始,可以一直看到他的這些作品大多描寫閉塞孤獨的"監禁"狀態,每每都在描述著一個個無法逃脫的有形或無形的監獄,人受困其中,進退不得,改變不了."遲到的青年"中安排著讓"我"嘗試要走政治的路,試圖做"政治的人".但矛盾的是"我"有陽痿,他甚至不是"性的人",這在意象上是大江小說常見的傳達手法,當人有權力,有威嚴,能夠掌控,妥妥的一個雄性特徵,勃起向上的超大陽具,反之,則是無能為力的代表,所以"我"是無性能力之人,也是無政治能力之人,只能被操控,這是雙面的意義.所以先安排他叛變政治家,這是他首次的自我挑戰,他果真與過氣女演員有了成功的性交,似乎在轉折中有所改變了他的命運必不可變的可能性,但是當他到了神戶與阿康過上虛無的生活後,卻發現那一切都像是偶然勃起射精後乏力,依舊回到了現實的苦悶,又回到了原先的思想道路.即使他毀掉了自己教養院的檔案,改以東京大學菁英分子的面貌出現,他也不可能改變自己被操控的人生,因為"遲到"已經造成了必然性,而這種無法改變的現象也潛意識的成了一種恥感的源頭,"我"經歷骯髒的政治鬥爭後想要反抗整個社會裡的不堪,但最後卻屈服於善於權術的政治家的賄賂,過上安逸的,不痛不癢的普通人生活.其中唯一令他羨慕的,是他表達了對一個自殺的十六歲同性戀美少年的愛,這份愛來源於他對那個人身上某種特質的渴望,比起金錢,地位,那是某種壓倒他整個人生的特質,在文本中,體現為澤田育子小情人不斷任性的與她發生關係,一再懷孕不用負責任,隨時都能逃離,爛攤子由他人負責,且兩次都是"我"來承擔,也根本不在乎對象是個老女人或是政治家的子女能有何種利益,甚至最終承認因自己同性戀,只是因為無法接受自己孩子的生死受別人操控的單純而自殺,死前還假意留書頂替了"我"的殺人罪責,面對這樣不幸又有力量的少年小情人,"我"只能感慨:我將會一直沉浸在唯恐罪行敗露的恐懼和那對不幸卻勇敢的少年的充滿自我嫌惡的卑怯的愛之中,並漸漸變成一個同性戀者",相比於"我"負罪恥感,自我意識缺失,小情人煩而活得很自在,隨興,自"我",是一個真正有"我"的我,而這是"我"一直求之不得的,而明顯的便是與戰後一代未受軍國思想洗禮的對比,可以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拋卻了集體他們的箝制.
慢慢的會發現,大江作品中呈現出來的都是"醜態",這種醜態主題與其他人很不一樣,與所在國家表現出的形象很不一樣,然後他也不是再說甚麼是非道理,而是藉由呈現出某些真實的樣貌與狀態,讓讀這自行去體會與感受,光是選擇完成這個題材就很不容易,畢竟在那個年代,那種時空,都算是一種尖銳的發聲嘗試,值得一看.以上.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